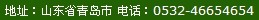|
读而思 duersi 讨白(小说) 文/李继林 大南沟在深山里,很偏远。大南沟没有路,沟底就是路,弯弯曲曲三十里砂石沟,下雨时流水,天晴时,雨水干了,沟底就成了大南沟人的路。虽说弯曲,还算平坦,拖拉机,摩托车突突突跑过。一辆车过去,机器声被山崖折来挡去,满沟突突声。当然还有架子车,自行车。骑骡马的人不多,但在大南沟经常能见到,多是年龄大一些的老人。有喜好唱歌的,伴着清脆的铃铛声,扯开嗓子漫一曲花儿,空旷的山沟就立码活泛起来了。那样的情景绝妙,可惜现在不多见了。 大南沟有三十几户人家,分散住在山坡上。南坡上全是黑土地,肥沃的很,只要撒下种子,就有收成。 有素老汉是大南沟年龄最大的老人。他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觉得这里很好,年轻人嫌弃,说大南沟太偏僻,走镇上都要三十几里路程。老汉说,老先人就是看中了这地方的偏僻,才在这里扎下脚,这里的土地养活人。 大南沟有一座清真寺,在村子中心,是大南沟最大最豪华的建筑,是村人汇聚的中心,是他们心中的圣地。大南沟的男人们每天都要到这里来礼拜,年年月月,从不间断。礼拜是他们的功课。每当梆克笃笃响起时,男人们便头戴着白帽肩膀上搭着白羊肚毛巾,从四方向清真寺汇聚。大南沟在梆克声的渲染下,显得愈发宁静祥和。 礼拜是有素老汉每天必修的功课,他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寺里,第一个和阿訇说色俩目。阿訇五十多岁了,很有尔领.带着一位满拉,二十刚出头,是有素老汉的本家侄孙。 阿訇是大南沟最忙的人,也最有威望。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离不开阿訇。阿訇除了每天主持清真寺里的工作外,还有许多事要干。给刚出生的孩子取名字,给逝去的人念素尔,给头痛脑热的人吹都哇,还要宰生。宰生的事一般都让满拉去干。最要紧的是念讨白,阿訇和满拉一起去。即将口唤的人,要是没人给念讨白,那是很大的罪孽,口唤后进不了天堂,真主那里不收。每逢有即将离世的人,其家里来人叫阿訇,阿訇就丢下手头的事,匆忙跟了去,满拉紧随着,一起去念讨白。没有比一个人口唤更大的事。 有素老汉家在村子的最北头,走寺里将近一里路程,他每天都要到寺里去礼拜,一口气走到,心不慌气不短。他的身体好着呢。这些都是苦了一辈子的结果,下苦干农活在他看来天经地义。没有苦死累死,倒是落下个好身体。他在这山沟里干了一辈子农活,从来没有感觉到过苦,就如吃饭穿衣,再平常不过。他把所有的事都想的很开,自己倒落个心闲。老伴在五年前先他口唤了,老伴口唤的平静而安详,丝毫没给他留下悔心。临完时,阿訇和满拉都在跟前,带了水,上了香,在炕头上念讨白,送她上路。有素老汉发现老伴断气后,面色红润,特别好看。这一发现让老汉很是安心。老伴和他一样是真心的信仰真主,一辈子没走出过村子,但她活的很滋润。他坚信老伴是走了一条向上的路。送完埋体后,他心里感到一丝孤凄,好在儿女们都孝顺,不停地陪伴照顾着他,慢慢也就习惯了。他每天最主要的事情是礼拜,礼拜已成为他生命里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他不知道除了礼拜他还会干啥,一天的时间如何打发。这几年他彻底的从农活上退下来,不是自己做不动,是儿女们不让他做。儿子说,年纪大了,该享享清福,再做活, 别人要说话。他也就随儿子的意,不再下地干活,除了给牛羊 添一些草料外,什么事也不管,一门心思都用在礼拜上。 近来有一件事让有素老汉特别难为,甚至有些伤心。这事他没有给任何人说过,他觉得给儿女们说这事有点羞于启口,给别人说了也白搭,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他一直悄悄的忍受着。有时自己暗想,是不是那里作的不对,或者礼拜时走了神,真主要惩罚他?这样想时,便感到一阵惭愧,回想自己这一生,很清白的,没欠过别人一分钱的帐,没作过一次见不得人的事。既是在小时侯或者年轻时代,也没犯过昏。他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胆小怕事。拿他家老人的话说,这娃娃脑子里没沟沟,出息不大。他自己也认命,出息了又能咋,还能把天踢个窟窿子?出息再大,照样吃饭拉屎,还能喝金尿银?他走着一条传统而规矩的路,他害怕在他生命的路上叉出什么意料不到的事,他难以相信自己是否有能力处理。他只能按照传统的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自己的汗水在土地里乞讨生活。其他一切全托靠真主。既是哪个动乱年代,清真寺被拆了,没了礼拜的地方,他也不间断的在自己家里礼拜,他相信那是整个穆斯林的灾难。他似乎很有预见性的说过,等到灾难满了,总会有个礼拜的地方,而且会更好。这些都被他说中了。但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在半道上出这么个事。真是半路上不出六爪,啥事都出呢。 有素老汉得了一个病。 他的下身靠右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出现了一个包块,大概在几年前,开始像鸡蛋大,不痛不痒,不碍事,就没在意。这东西很奇怪,好象一直在长,睡觉时它就不见了,也去睡觉,走路时它就出来,重重地垂下来,搅祸的连路都难走,现在有萝卜大小了。最近一段时间,他被这个东西搅扰得很不安宁。平时,他把手伸进裤兜里,使劲地按住肷窝哪个出口,那东西就被堵在肚子里规矩的呆着,可做礼拜时,他不能用手去堵哪个口,它就钻出来捣乱。有时还咯咛的痛一下,使他不能静下心来礼拜。有一次,他在水房里洗完大净,刚到大殿里跪下来,那东西就咕噜噜涌出一大包,刀绞一样痛的他满身大汗。他没法做礼拜,只好平躺在大殿里,自己忍着劲把那一包东西往肚子里填。等他平静下来时,礼拜已经作完了。那是自他会做礼拜以来这么多年,第一次在大殿里没有完成的礼拜,他满脑子悔恨和自责,他觉得那是对真主的极大不敬。同时他也明白了,他得了一个病,这个病可能不会要他的命,但这个病会严重影响他做礼拜。这个想法对他来说是一种致命的打击,这样想时,很快要被自己的想法击倒了。他感到了自己的虚弱和无能。突然间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他在这个世界上活了将近八十年,却对自己的身体一点也不了解,如果不是身体出了问题,他好象从来没有在意过。这身体是自己的吗,那为啥由不得自己做主呢。他可以拆毁一座房子,建起一座大殿,可他却对自己身体上这一点点小问题无力解决。他不是害怕死,其实死对他来说已经是一种亲切的向往。他坚信当口唤到来时他会随着真主的召唤,进入向往已久的天堂,那里有他的老伴,有他的亲人,他们幸福而永恒的生活着。他感到害怕的是,一口气不断,而却不能礼拜,那样活着还有个啥劲儿。 有素老汉决定去看病。 他没有告诉儿子真实的目的。医院里去看看满子。儿子说,等满子出院回来了再看也不迟。他瞪了儿子一眼,不说话。自己坐去镇上赶集的拖拉机走了。 满子是有素老汉的侄儿,得的是急性阑尾炎,前天在地里干活时,突然肚子痛的要死要活。医院时有素老汉看过,人已经变了形,圈成虾状,脸上直冒生汗。据老汉的看法,大概是口唤要到,那么凶险的病,明着是要命呢。可回来的人说,镇医院有个大夫,当天就给作了手术,从肚子里倒腾出一大碗黄脓。今天已经好多了,能下床来自己尿。老汉为自己的看法惭愧了一会,突然就有想法。听说现在的大夫能的很,看样子不假。他这一辈子最远就去过县城,那还是多年前的事,最近几年连镇上也很少去了。想不到镇上的医生,会动手术,幸许自己这病也能动手术给取了,再利索的活上几年,那不是胡大的慈悯么?这么想时,自己感动的快要流下眼泪来。他甚至想到自己在大殿里虔诚的作着礼拜,大殿里温暖而肃穆,笼罩在神圣庄严的气氛里。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映射在五彩的地毯上,洁白的墙壁上,幻化出神秘的光,在那光里面,流动着一种难以扑捉的气息,慈祥而温馨。那是不是真主的气息,真主的光泽呢?想起哪次因疼痛而不能完成的礼拜,医院的决心。他的内心突然间充满了力量,仿佛一下子年轻了许多。 满子在病床上躺着,手背上插一根管子,架子上瓶子里的药水顺着管子流进胳膊里去。有素老汉看的发呆。病能这样子治,稀奇啊。满子气色很好,不象得大病的人,招呼老汉在床边上坐。老汉说,还痛吗。满子说,不痛了。老汉说,作手术时痛吗。满子说,没一点感觉。老汉迷茫的点头应着,满脑子的疑问。不是要动刀子吗,刀子割肉,能不痛吗。正想着,大夫进来了。满子说,这就是李大夫,给我动的手术。老汉便从床上弹起来,恭敬的站着,想伸手去拉一下大夫的手,又怕唐突,只好缩了回来。倒是大夫和气,主动伸手过来,老汉便抓住救星一般,激动的快要掉泪了。他觉得这双手在一直等待着他,他也在努力的寻找着这双手。这是一双多么灵巧而神奇的手,它会使生命起死回生。这双手就偏偏让自己给抓住了,这是一个宿命,是真主的慈悯和眷顾。老汉仔细的打量着大夫:年轻,精干,待人和气。就是他了。老汉心里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打定了注意。这是真主的安排。老汉想。 有素老汉决定把自己的情况说给李大夫。这也是他今天来镇上的目的。从一见面,他就肯定了要把自己交给这个年轻人。他相信自己的判断,他甚至觉得这个大夫很是面熟。好象在那里见过似的,那白褂,那眼神,说话的口气,举止神态,和他想象的一模一样。他想不起在那里见过,努力的回忆自己的经历,终究没想起来在那里见过这个年轻人。他的经历很是简单,几乎没出过远门,一辈子呆在哪个山沟里,认识的人能够算得出数,那里见过这个大夫呢。但确实面熟,他不能否认自己的感觉。他很黏糊的问李大夫的有关情况,大夫好象不大乐意说,躲躲闪闪的,只说他当医生十来年了,学的是外科,能作些简单的手术。医院条件太差,设施跟不上,作手术比较冒险。满子见老汉话多,怕惹大夫嫌,不停的使眼色,老汉看见了,就不再黏。见大夫要走,就说,我有个病,想麻烦大夫给看一下。大夫说,跟我到办公室去看。老汉便跟了大夫到办公室里,坐在小凳子上,把手伸过去。大夫说,那里不舒服直说,我不会号脉。有素老汉有些吃惊,那有不会号脉的大夫。是不是他嫌弃呢。心里有些不快。但看大夫的神情不象是嫌弃,只好照实述说自己的病情。他说的很详细,生怕遗漏一点线索,他从来没有向别人说过自己的病,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要看这个病,再则,他觉得难为情,这病长的实在不是地方。这一次是铁了心要看病,就顾不得其他了。大夫专心的听着。等他说完了,大夫说,你这病叫疝气,老年人常见的。我给你检查一下,看能不能做手术。老汉听说,心里就温暖的要开花,任凭大夫摆布,从上到下,让大夫检查个透彻。大夫让他褪下裤子,用手把哪个包块推进肚子里。他丝毫没有感到难为,听话的像个孩子。他觉得大夫的手温暖而轻柔,充满神奇的魅力。那手指从他的皮肤上按过,他的疾病正在消散或愈合。他似乎已经从痛苦里走出来,健康而宁静。他在心里暗暗祈祷,胡大呀,慈悯我吧。 但大夫的话却让他失望。 大夫说,你的病完全可以作手术治好,但你的年龄太大,我们这里条件有限,医院去作吧。花不了多少钱,几天就好了。 老汉心里突然就结了冰。 老汉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不是他要听到的话。但大夫确实这样说了,看大夫的表情,没什么异样,不象是骗人或推脱。但问题出在那里,他一下子弄不明白。年龄和作手术有关系吗,肯定不是。是不是……这样想时,老汉心里就又升起一丝希望,像一串火苗样燃起来。他不敢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他知道这些事是不能说出来的,但他知道该怎么作了。他相信这个年轻人,他看到大夫的手干净而灵巧。医院,县医院对他来说很遥远,从没想过,也不敢想。都是黄土淹到脖子的人了,医院去作手术,划不来折腾了。他相信眼前的这个大夫。这也是他一辈子的习惯,认定的人或事,瞎好就不想变。 老汉临走时笑着说,就是你了,我认定了你,就信你。口气坚决的不容改变。大夫没说话,有些吃惊的看老汉拄着拐杖走出去。那背影像一棵古树,苍老而挺拔。 下一个逢集日,一大早,有素老汉就把儿子叫到跟前,说,把那只最肥的老鸡公叫阿訇宰了,今儿个要到镇上去。儿子说,宰鸡公干啥。老汉说,去看李大夫。儿子说,李大夫又没给你作手术。老汉就嘈了,拿眼睛瞪儿子。儿子向来听话,就不敢再问,抓了鸡公去寺里。到寺里问阿訇,阿訇也说不知道老汉是咋了。儿子觉得老汉一定有事瞒着他,就叫阿訇到家里来跟老汉拉呱。儿子在院子里收拾鸡,阿訇和老汉在炕上拉闲,老汉就把要作手术的事给阿訇说了。阿訇很是感动,把儿子叫进来骂了一顿。说你这后人是咋当的,老人病了多长时间了,也不过问一声,到要老人自己张罗着看病?儿子一脸的冤屈,说,不知道吗……阿訇说,还犟嘴?不要再说了,张罗钱去。儿子说,钱不是问题。阿訇就笑了,说,那就好,我今儿个和老汉去一趟镇上,把日子定下来。 镇上逢集,街道里人多的无数,各色商品更是琳琅满目。老汉顾不得看一眼。拉医院里去。从窗口里看见李大夫在上班,老汉没有直接进去。给阿訇说,要是他还不答应,咱们就找院长,你看行吗。阿訇说,你先进去说着,我把院长拉过来帮腔。老汉说,那再好不过了。就进去了。 有素老汉坐在大夫旁边时,心里说不出的紧张。他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一辈子没在人前头说过话,也没有给人送过礼。一路上他把要说的话想了不下一百遍,可到了跟前,却难为的一句都说不出来。那只鸡儿子收拾的很干净,装在袋子里,他想直接把鸡放在桌子上,又觉的不托。他得先把话说好了。大夫笑着对他点头,给了他许多勇气,慢慢的平静下来。老汉说,认得我吗。大夫说,要作疝气的吧,记得的。老汉说,你的手艺好着呢,满子现在好人一样,能吃能喝。大夫说,要好呢,不好就麻烦了。老汉说,那你就给我也作了吗。大夫说,你年龄太大了,有风险。老汉说,啥风险,不就是个手术么,我都八十岁的人了,还能活几天,只要你给我作了,能让我利索的活上一天也算,我要礼拜,我是穆民,我咋能不礼拜呢,可这病折腾的我没办法礼拜,你说我活着还有个啥劲儿。刚跪下来,它就咕噜一下子冒出来,不能礼拜。那是在大殿里呢,胡大要怪罪呢。我给你宰了鸡,我家里最肥最大的鸡公,我举意了,你要稀个勿巴哩呢,哪怕是作着无常了,我也不怪你。我就是认定了你,就信你……老汉被自己的话感动了,眼睛湿润了,分明要流下泪水。大夫很是吃惊,不知如何说好。 院长和阿訇进来了。气氛缓和下来。阿訇又说了许多好话。有素老汉说,好的很,好的很,人么,活上多少是个够。又说,要是怕万一有闪失,临上台之前,叫阿訇给我念个讨白,也算圆满。听老汉这么坚决,大夫就答应了。有素老汉说,就是么,就是么。便激动的流下泪水来,握了大夫的手使劲的摇了半天。 这是一个秋天的早晨,大南沟笼罩在淡淡的晨雾之中。空气清新而湿润。前天下过一场大雨,把村庄冲洗的很干净,村里的树木,山坡上的野草,翠绿翠绿的。远处山地里还没收割的秋庄稼,绿的一坨,红的一坨,黄的一坨,像一幅鲜艳的水彩画;沟底里一股清澈的溪水,逶迤着向山外流去,发出细微而悦耳的声音,沟畔上悬挂着长长的野草在微风里舒展的摇曳着。偶尔有山雀婉转的啼鸣从草丛中传来,使大南沟显得愈发安静而祥和。山头上挂着一块棉絮一样洁白的云,被巧手的女人撕化了一般。太阳刚从东山露出了头。 有素老汉今天很高兴,脸色红润,精神饱满,好象年轻了许多。他的表面上看起来很安静,但心思却转的飞快。大殿里神奇变化的光,大夫那双灵巧的手,阿訇念经的声音。他甚至想象手术室里的情景,可他实在想不出手术室是怎么一回事,他肯定那是一个十分神秘的地方,不是他能想象得出来的。但此刻,他觉得那地方亲切温暖,是成就他的心愿的地方,他愿意在那里被大夫割开肚子。他想象大夫的手术刀,很长,很锋利,散发着冷冷的寒光,从他的肚皮上轻轻走过去。有一丝恐惧的念头刚从内心里升起来,很快就被他压下去了。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卑微,正是这卑微的念头,牵引出了他的镇定和从容,一种赴死的决心让他很快又变的坚强而勇敢。 儿子在院子里收拾拖拉机,媳妇找出干净的衣服让他换上了。他在等着阿訇和满拉过来。早晨礼拜时已经说好了,阿訇医院里,给他念讨百。 阿訇进来时,后面跟了一大群人。有本家的亲房,有村里的老人。他医院作手术,他们都在今早洗了大净。 有素老汉看见这么多人要陪自己,心里就涌上来一股热流,冲到眼眶里了。 因为去镇上的人多,就开了两辆拖拉机。有素老汉和阿訇坐在一起,出村子时,回头看,觉得怪怪的。生活了快八十年的地方,突然间好象陌生起来,平时没怎么觉得,这时候有点离不开的样子,是不是这一去就再也看不到他的村庄了呢?一丝忧虑悄悄滑过心里,接着涌上来的是一丝酸楚的留恋。老汉仔细地看着村子里的一切,弯曲的小路,恢恢的泥墙,嫩绿的树木,高大雄伟的清真寺……他贪婪地看着,似乎要将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装进自己的记忆里去。两滴浑浊的泪不觉间就挂在了苍老的脸颊上。阿訇发现了,就笑着说,看你的样,像是真要去见胡大了。有素老汉就回过神来,说,见胡大不怕。你说咱这大南沟咋就这么好呢?一句话说的一车人都楞了。 拖拉机到了镇上,镇上逢集,人山人海的,医院方向开去。到了镇上清真寺门口时,阿訇叫停下来,说想去看看镇上寺里的阿訇。其他人就在街上等阿訇。一会就见阿訇出来了,镇上寺里的阿訇也出来了,还跟着好十几个满拉。医院去,他们后面走着来。 有素老汉要作手术的事已经在街上传开了。见两位老阿訇医院走,就有几个人跟着来了,医院时,跟着来的人就有了一大群,黑压压站了一院子,洁白的帽子像一朵朵盛开的花。大夫见来了这么多人,不知就里,出来看。阿訇拉了大夫的手说,都是来给有素老汉念讨白的。大夫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他很迷茫,有点弄不明白的样子。 接着就见人们神情肃然,一种庄严神圣的声音浑厚地传出来,医院,飘过街道,飘过山峦,飘到云霄里去了。 李继林,西吉县将台乡人,现在将台乡卫生院工作,嗜好文字。 推荐:北京哪家治白癜风能治好吗中医治疗白癜风哪里好
|
当前位置: 阑尾炎疾病_阑尾炎疾病 >特别推荐小说讨白李继林
特别推荐小说讨白李继林
时间:2016-12-19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艾灸能否治百病解答nbsp,今天继
- 下一篇文章: 水是最好的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