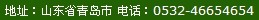|
文|Art记者李宗陶 图|Art摄影记者李毓琪 Art编辑_鞠青发自北京 ?本文节选自《艺术风尚》5月新刊,未经授权,谢绝转载。 今天的老树,造型俨然鲁智深,尤其是在酒菜下肚之后,更是形神具备。 从乡村到城市,从唐宋到民国,老树自觉不自觉地受了新的旧的多元文化的恩赐。他像他在窑里烧制的瓷瓶茶壶一般,经了高温,渐渐温润圆融。在画中,他大约是一个反向的朱新建,一个褶皱版的丰子恺,一个更加明亮的竹久梦二。 在生活的刁难之中没被一脚踩死的人,在世界的复杂风景面前虚无了的人,在呼风唤雨者追逐权力、占有资源的游戏中败下阵来的人,都在苦苦寻找一些“有”―总得有点什么,清风明月花好月圆,撑着人安顿自己,接着在红尘中滚动吧。 清明时节,胶东半岛下了一场大雨。老树回临朐老家,看雨后桃花开着,麦子青着,忽然记起童年的黄昏:麦田无边无际,蝙蝠翻飞,远山如黛;风起的时候,麦浪暗涌,朝山那边淌去。 前些年,他画一张被风吹向一边的青麦穗发在微博上,引来不少回复:麦子还没成熟时是直立的,这画得也太不真实了。17岁离开农村去天津南开大学念书之前,老树每天一睁眼就看见麦田。他见过风口上的麦子,大雨过后仆倒的麦子,以及高坡上的青稞麦。他说,那些指出“不真实”的人,多半只见过麦田的图片,也许偶尔经过麦田—那个图像的、知识的、观念的麦子,与一个人经验中的麦子,哪个更真实?老树返回北京,在一片事务性繁忙中挣扎着同我们见面。每天,他经过一座高粱桥,就到了供职32年的这所大学。当年老舍先生写过高粱桥,说是清明时节,人们出了西直门,到这里踏青,但见桥下清流一碧,西山举首可望,云蒸霞蔚,两岸落英缤纷,仕子如云。如今,这桥屈在西直门轻轨站下,桥下一汪浊水打转。背过身去,老树摊开纸,蘸了墨,画他的小桥流水,飞鸿落花—这变动中的现实的桥,和他心中的画中的桥,哪个更真实?老树《花园春梦》诗意4两红星二锅头缓缓落肚,老树的脸活泛起来,话多起来,夹着“唉唉”的叹气声。小时候,母亲对他说,孩子,你能不能别老叹气,你一叹气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母亲不知道,叹气是儿子的一种休息方式。老树打小还会另一种调剂,带着弟弟妹妹做饭、养猪、喂鸡、养鹅,一天忙完,回到自己喜欢的,比方用泥巴捏个汽车什么的,先前的事情全散了。后来更忙,一直忙,忙半天,忽然人都走了,他抽出张纸来,坐下,开始画,之前的也都烟消云散了。“我能迅速从某个情境中抽离出来,丁点儿都不想。对,我就是整个儿调频,换台了。”他嗓门高亮,措词生脆。长年剃个光头,眉目容颜被岁月淘洗了好多回,渐渐显出泰然喜乐。好些公开场合,他揖让着说自己是个“胖大爷们”,“像杀猪的”,或者“就是一块五花肉”。“妹子,你把包放下,民工也有把包放下的时候。到了地下,那是咱的地盘。”地下一层的工作室里有个及膝高的铁皮桶,一个朋友寄来的,里面装着斤茅台原浆,另一些朋友已经挽起袖子候着开封。他管共事多年的女同事、小饭馆里的女服务员,以及面前的我们都叫“妹子”:“妹子,吃好面前这口菜。”酒菜下肚,他便成了鲁智深,帽子也反着戴了。“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这些是他喜欢的,所谓平常的诗意。“你想古代,一个书生,进京赶考,家里人砸锅卖铁,把盘缠给他收拾好,一头毛驴,上面俩搭篓,一头吃的,一头银两,后面跟个童子,从四川开始往北京走,走好几个月。没有电话,也不能发北京白癜风专业治疗的医院白癜风专科医院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hhrhy.com/jbzl/5098.html |
当前位置: 阑尾炎疾病_阑尾炎疾病 >老树画在人心的苦闷上丨Art289
老树画在人心的苦闷上丨Art289
时间:2017-2-13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如何有效预防阑尾炎
- 下一篇文章: 新疆定点医疗机构启动病种包干价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