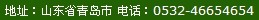|
山东白癜风医院 http://pf.39.net/bdfyy/bdfzj/171111/5837448.html 文 张得膘(一号哨位专栏作者) 某日在家清理杂物,我在抽屉深处发现了一本相册。上面已经落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我轻轻擦拭去了封面上的灰尘,打开相册,一张张熟悉的脸庞出现在了我的眼前,刚子,大伟,阿创,黎叔,豆豆…… 那些人,那些事,那些话语,宛如就在昨天刚刚发生过的事情一样,仔细回想,却又模糊的很。不禁心里百感交集。人的这一生真的实在是太过短暂。从蹒跚学步到成家立业,仿佛就在转眼之间的事情,快得让我们措手不及。 想起了原来念书那会儿英语老师曾在课堂即兴教了我们一句特文艺的句子:Weoftentellyourself,dontforgettodontforget,butwiththepassingyears,finallywestillforgeteachother.中文翻译大意是这样的一句话:我们时常告诉自己,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却随着岁月的流逝,终于我们还是忘记了彼此。终于我们还是忘记了彼此。 照片会泛黄,记忆会冲淡,唯用文字去记住他们,去勾勒出他们的轮廓。笨拙的去重新塑造记忆中的他们。真可悲啊。 一 年冬,前段时间湖北刚下了一场大雪,那年积雪还没化尽,花坛边,泥土里,长停放街边的车顶上。斑驳的白色遍布在整个城市。 我被接兵的班长老阮领进一间集体宿舍,望着陌生的环境,我一时不禁恍惚了一下。 这是你的床铺,班长老阮看了一眼初来乍到还没回过神的我说。指了指靠窗的一床空铺,这里不像地方,到了这里,你得尽快忘记以前的身份,一切都得重新开始了。哦,我立刻回过神来,赶紧点头应道。别说“哦”,老阮认真的看着我说,得说“是”。我一愣,想了想,老实的点点头,哦,知道了。老阮一窒,翻了个白眼,让我简单的休息一下,就出去了。老阮是我新兵团的班长,才二十岁的年纪,却因为常年在部队磨练缺少保养的缘故,长着一张大叔脸。 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宿舍,想起了老阮那张饱经风霜的脸庞,不禁对自己未来的日子感到深深的忧虑。屁股还没坐热,一阵凌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便有四五个穿着荒漠迷彩服的人涌了进来,带头先进来的是一个魁梧汉子,见宿舍多了一个陌生人。先是一愣,随后明白估计是新来的战友,纷纷热情地朝我打招呼。我点点头,礼貌的笑了笑,表示回应。 这时一个长着一张麻将脸的哥们,最后一个扶着墙走了进来,一瘸一拐的抽出床底下的小马扎,艰难的一屁股坐了下来,顺势把左脚迷彩鞋一脱,顿时本来就不大的宿舍里,充斥着一股陈年的老坛酸菜的味道。那魁梧大汉被那汗脚熏的面容扭曲,豆豆你能不能在门外脱去,好大的味儿知不知道?那个麻将脸一边脱袜子一边抱怨,哎哟我擦,阿创你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啊,豆爷我今天跑步腿都跑瘸了,你看看你看看,说着一提裤腿,露出微微肿起的脚踝。又翻开长着一颗水泡的脚掌,水泡还挺别致的长在大拇指的前端处。 自称豆爷的麻将脸哭丧着脸抬头望着阿创,你说说这叫啥事儿啊,今儿第一次跑了个三公里就差点要了哥的老命,这以后的日子该咋过啊,哎哎,你那不是有针么,借我使使。阿创闻言,一脸警惕,你要干嘛。难不成你还会针灸?豆豆的麻将脸白眼一翻,配着肤色,活脱脱就是一张白板。针灸你妹啊,借我戳水泡啊。阿创大叫,我擦,要不要这么恶心,那是老子用拿来缝衣服的!哎哎哎,都是一个班的战友,就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嘛。 经过一番激烈吐槽后,阿创无奈的从抽屉里的针线盒内挑出一根绣花针,心疼的递给了豆豆,并对豆豆诚恳地表示不用再还给他了。豆豆如获至宝般接了过来,便不再理会我们,埋头小心翼翼的戳着水泡,不时嘴里嘶嘶倒着吸冷气。 我在一旁将这些看在眼里,悄悄地叹了口气,仿佛在豆豆的身上看到了未来的自己。想想自己的渣体质,悲观的感觉到自己的未来军旅生活前景堪忧。当本很森福德,类搜捕搜得鸟?一直都靠在床架边,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突然冒出了一句话。很认真的盯着我,眼神似乎还带着些许怜悯。从进门到刚才,他都沉默寡言在一旁默默的喝水,没说一句话,却一开口就说了我听不懂的语言,我有些茫然的盯着他,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我缩,当本很森福德,类搜捕搜得鸟?见我还是一副茫然的表情,他有些急了,涨红着脸叽里呱啦说了半天,似乎想极力纠正自己的发音,却依然像是嘴里塞满了馒头般含糊不清。他说,当兵很辛苦的,问你受不受得了。阿创哭笑不得的看着我们猜哑谜似的两个人,好心在一旁解释充当翻译。顺便向我介绍了一个班的同志。刚才说话含糊不清的,是个广东人,叫黎叔。埋头戳水泡的是豆豆,靠在窗台写信的,跟阿创一样魁梧的大高个是阿创的老乡叫大伟。而那个自顾自缩在坐在墙角边的地上假寐的小个子是刚子…… 还没等我一个一个的打招呼,班长老阮就走了进来。豆豆满怀期待朝老阮展示了自己的伤患处,想借此机会休息两天好好养伤。得到老阮果断的拒绝后,哀嚎一声,便垂头丧气的继续和脚底板的水泡进行殊死搏斗。老阮看我还是一身羽绒服便装,皱了皱眉头,等会你就跟阿创去仓库领装备,赶紧把你这身地方衣服换了,还有你头发这么长,等会儿豆豆去隔壁班借把推子把你的头发给理了,刚子你别装睡,你也一样要理!你身上的那些地方习气要尽快消失掉。虽然你这是第一天来,但是还是得有一个兵的样子! 头发很长吗?我愕然的摸了摸来新兵团报到之前特意去剪过的平头,不过当我看到屋子里除了我和班长,其他的人基本都是三毫米的劳改头,虽然心里不由泛起一丝反感,但我没将情绪露出脸上,而是默默地点点头。 二. 唉,对了,你原来是干嘛的啊?在仓库里,阿创和我正在蹲着把新发的装备折叠起来塞进包里,他从出了宿舍楼就一直在找话题和我攀谈。我不咸不淡的回答,学生。哦,难怪我看你带着一股书卷气,我原来是在钢铁厂打工的,看到镇里招兵我就报名过来了。妈的,坐了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呢。阿创爽朗一笑,露出一排因为抽烟过多而被熏的有些泛黄的牙齿。呃,为什么不念书呢。 我有些讶异,眼前这个人的年纪并没有比我大多少。也就二十来岁。大好的青春不念书,为什么要去涉足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陌生又有点危险的社会。嗨,书念不进了呗,阿创拿了一顶雷锋帽漫不经心的在手里把玩,随手扣在自己的脑袋上。而且我跟你们这些城市兵不一样。我是农村的,家里环境也不好,所以……你懂的啦。嗯。我点点头,每个人要选择什么样的路,都是自己的自由,至于走得怎么样,就属于个人的造化,没必要盘根问底的打听。阿创是,我也是。 等我们提着大包小包的被装回到宿舍的时候。豆豆正在给刚子理发,别说还挺专业的。一边有模有样的拿理发剪细细打理刚子的头发,一边半蹲观察着桌上巴掌大的镜子内的刚子,看发型有没有理偏。刚子是个急性子,繁杂的程序搞得他浑身上下不舒服,忍不住对豆豆说,哎哎,差不多就行了,只是剃个劳改头,要不要这么麻烦啊。一听这话,豆豆不乐意了,这怎么能行呢!班长将这个理发重任交付给我,是对我的信任!怎么能够随随便便潦草了事呢。咱们当兵的,做啥事情就得在心里有个标准! 说着豆豆老学究似神气的摇头晃脑了起来。刚子乐了,哟哟哟,还挺有职业道德的呢,那豆大师,估计你给别人理发里的次数挺多的吧?豆豆语气羞涩,哪里哪里,加你才第三次。哦.......呃,纳尼?刚子一听傻眼了,勉强稳定住心神。声音不自觉带着颤抖,那,那你都给谁理过发。豆豆想了想,唔,好像是黎叔和隔壁班的一哥们吧?那哥们叫什么来着?哎呀,连队那么多号人,我哪里记得清啊。哎哎哎,你别乱动啊,头发理歪了可别赖我! 刚子颓然坐回了椅子上,声音隐隐带着哭腔,哎哟豆爷,您老这手可得稳住啊,黎叔那跟驴啃地似的头发敢情还是出自你手,我说他这几天怎么闷闷不乐的,连吃饭都要戴着迷彩帽。你要是早说,打死我都不敢坐这儿啊。豆豆一听勃然大怒,出于职业道德,手上的动作却不停,咋啦咋啦,不经历风雨怎么能够见彩虹,不经过摔打磨练咋出精兵?有了前面的教训,你觉得理发这种熟能生巧没什么技术含量的玩意儿还能难倒你机智的豆爷? 正说着,就听到班长的声音在门外远远的传了进来,豆豆过来一下,帮我拿个东西。到!豆豆猛一回身大声应了一声,手上的理发推子却好死不死“吱”的一声从刚子的脑门前一划而过。房间瞬间死一般的寂静刚子心里一凉,嘴唇颤抖着,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哆哆嗦嗦的伸手拿起桌上的镜子。拿到自己的面前。沉默了三秒后,整栋宿舍楼都可以听到刚子撕心裂肺崩溃的哭嚎。声音悲凄之极,闻者无不唏嘘不已,令人催人泪下。哎哟卧槽!老子的眉毛啊啊啊啊!!! 三 说老实话,那个时候的我并不喜欢阿创。也许是不喜欢他因为过去常年在社会打拼,身上带着那多年待在象牙塔的我不曾具备的人情世故的油滑。也许是不喜欢因为他仿佛都和每个人关系很要好,却从不敞开心扉的距离感。又或者是其他的,具体是什么,我说不上来。反正我就是不喜欢。也许是毫无道理的不喜欢。 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自己,对待喜恶的标准简单粗暴得令人发指。直到许多年后的某个早晨洗漱的时候,无意间抬头,面对着镜中那张湿漉漉的脸,也许是年岁渐长的缘故,眉眼间早已没了刚到新兵团那会儿的稚嫩,下巴还残留着没剃干净的泡沫和胡渣,当初那些自己憎恶的习惯和腔调,在这些年里,渐渐的一点一点的显露出来,自己却恍若不知。镜中的那张熟悉的脸仿佛是一个陌生的人。那个时候,我开始慢慢理解了阿创。也许,这就是成长的代价。 四 新兵团的一件事,让我开始逐渐转变了对阿创的看法。原因是因为在某天查出了阿创患上了阑尾炎。阑尾炎并不是什么大病,但是要命就要命在阿创这病得的不是时候。这时的新兵团训练已经临近尾声,三个月的训练,要出点成果的同时,评功评奖自然是少不了的。各连新兵们都是争强好胜血气方刚的少年,一个个摩拳擦掌的盯着优秀新兵和团嘉奖跃跃欲试。非得争出个排名先后。 而每个连队,优秀新兵的名额只有两个。阿创在连队里,无论是内务还是军事训练,在新兵中都算是拔尖的。老阮对他也是寄予厚望,时常在我们面前夸阿创是我们中间最有兵味的兵。连队优秀新兵名额中,必有的他一席之地。阿创要想治病,就必须的动手术,但如果动了手术,那么,阿创在下连队前的这段时间,基本算是暂时报废了。别说训练能不能跟得上,这一段休养身体的空白期,足以让阿创这三个月的辛苦付诸东流。 阿创是个很有野心的家伙,为了争优秀新兵的名额,查出结果的那天晚上,他和老阮在房间里谈了很久,最后决定对外隐瞒病情,忍受阑尾炎带来的病痛,硬生生扛了一个多月。那段时间,天天像个没事儿人似的坚持训练。直到最后在床上都痛得爬不起来了。才被晚上查房的连长发现情况不对,医院控制住了病情。这件事情才在连里传开。为此老阮还被排长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说他不关心自己班里的战士。差点耽误了治疗。为此老阮也只能无奈苦笑,老阮比我们更清楚阿创对待这个优秀新兵荣誉的重视程度。没过一天,阿创不顾医生劝阻回来了,坚持要用药物治疗。因为这件事儿,到了新兵团评功评奖的时候,阿创也如愿以偿的得到了优秀新兵的荣誉。望着台上和其他获奖新兵们标杆似的站在一起,脸色苍白但依旧意气风发的阿创。我心里没由的一阵酸楚。 五 值得吗?评功评奖的前一天晚上,我和阿创躲在天台,我终于忍不住道出了这段时间一直藏在我心底的疑问。老实说,我无法理解阿创当初的举动。为什么还要赔上自己身体的健康,去争取一个在当时的我看来无关紧要的荣誉。 阿创没有回答我,而是小心的从上衣口袋摸出两根皱巴巴的外出看病时偷偷带回来的劣质香烟,眼神示意问我要不要来一根。我摇摇头,不会。阿创便不再理会我,我看着阿创贪婪地吸着烟,像个瘾君子,烟头的火光一明一灭。一直狠狠抽到了烟嘴,才恋恋不舍的放下。我觉得值得,他看着我,隔着氤氲的烟雾,悠悠的说,仿佛是在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我知道你们在这件事情上觉得我像个傻逼,但是啊,我还是觉得这是值得的。 我跟你们这些城市来的孩子们不一样,你们有些家境好的、有关系的人,当兵两年回去后,家里就可以安排工作。我不行,我家里没钱啊,我爸常年在外头打工,他年纪大了过个几年就干不动了,我妈身体不好,弟弟不像我,他有出息,以后还要念大学,可以说全家人以后得靠我养活,部队里竞争激烈,如果一开始不在部队里混出个名堂的话,到时候想留队就会很困难,而且我也想把我上台领奖的照片寄回去让我妈高兴高兴。 说着烟头丢在了脚边,用脚用力碾了碾,火星四溅,随即暗淡消失,像是他瞳孔里熄灭的光。擦,这人生真他娘的扯淡。耳边仿佛传来阿创的低喃,想要仔细分辨,却被风声掠过了耳朵。 我们一直行走在岁月的旅途中,看不见来路,也望不到尽头。 晚安。 张得膘我记得你
|
当前位置: 阑尾炎疾病_阑尾炎疾病 >给你三秒钟,你能记起新兵连的几位战友
给你三秒钟,你能记起新兵连的几位战友
时间:2021-8-7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三个特别毒的爱情故事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